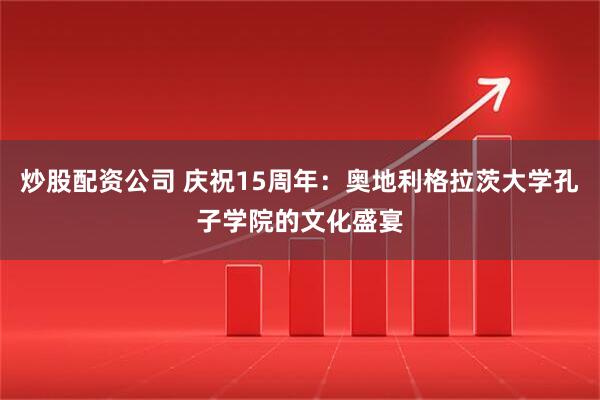1978年9月14日凌晨炒股配资公司,北满的夜风透着寒意,邓小平的专列在陶赖昭车站缓缓停下。站台上看不到仪仗,也没有欢迎横幅,只有李力安匆匆赶来。就在这股热气腾腾的蒸汽声中,一场被他本人称为“点火”的行动走向高潮。
火并非真的火焰,而是打破僵局的信号。邓小平喜欢用这两个字,原因很直接——火起得快,燎得广,还能逼人向前跑。他对李德生笑道:“这里、广州、成都,都得冒点烟。”

东北行的首站是大庆。石油城连日阴雨,泥浆裹着工棚,可钻井架依旧林立。陪同人员递上日程,他摆摆手:“先去井场看看,别让人等。”现场机器轰鸣,钢索拉得山响,工人们抬头行军礼。邓小平盯着转盘的速度,沉吟半晌,只说了五个字:“设备得再换。”语气轻,却像锤子砸在地面。
离开大庆那天,他在车上对陈烈民提了三件事:先进设备、物质奖励、老工人再培训。末了自嘲道:“可别把我当圣人,我只是催催火。”随行干部听得摸不着头绪,却能感到这位老人把“现代化”三字反复掂量。
火种最早撒在南粤。1977年11月,邓小平复出不久,到广州待了九天。珠江两岸破旧而热闹,逃港、缺粮、缺外汇,问题像竹筐里的蟑螂,一掀盖就乱窜。有人汇报:“有的公社规定养三只鸭子算社会主义,五只鸭子就犯资本主义。”邓小平眯眼:“怪事,连鸭子也分成份?根子在政策。”话一出,会议室里没人再提“阶级帽子”,只剩“怎么活”三个字。
他给广东留下两句话:过去好用的土办法能恢复就恢复;能自己解决的事别等中央批。说完便北上,把摊子留给本地干部。有人暗暗叫苦,也有人豁然开朗——城市贸易点活了、乡下自留地松绑了,偷渡的人少了。事实胜过十份文件,这就是第一把火。
第二把火燃在成都。1978年初,他结束缅甸访问回川小住。省里领导拿“包产到组”的材料犹豫再三,终究还是递上去。邓小平翻完报告,扔下一句:“三只鸭子那事儿你们也听过吧?农村同样缺口子。”当晚,四川省委给各地放行,允许副业自留、包干试点。很多人事后回忆,那天像久旱后的闷雷,一响就知道雨快来了。

若说南方两处是探路,东北就是点醒思想的舞台。9月16日,在长春南湖宾馆,他开门见山: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,思想僵了,手脚就束。”紧接着提毛泽东“实事求是”的老传统,用意很明显:路线不拧正,现代化只是口号。听众里不乏老干部、技术骨干,他们真切体会到这番话不是空洞口号,而是对多年沉疴的外科手术。
17日抵沈阳,李德生等候在司令部简易招待所。两人边喝浓茶边闲聊。邓小平突然把茶杯往桌上一顿:“我是到处点火的,在这儿也要点一下。”李德生一愣,随即明白:军区要为地方建设让路,要为科技更新站台。不多久,“军转民、军民合用”成为沈阳机床、抚顺石化的常用词。
短短两个月内,南北三处“点火”带来三个直观信号:政策可调、试验可搞、思想可松。它们像三支探照灯,把多年封闭、匮乏、惧改革的阴影照得通透。更重要的是,各地干部终于发现——中央不仅允许试,而且鼓励先闯。胆气被点燃,比任何物质奖励都来得猛烈。
值得一提的是,这一年五月,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在《光明日报》亮相。文章掀起思想解放大潮,邓小平却身在路上。记者问他看法,他淡淡地说:“讨论得好,我就在实际中再添把火。”这句含糊回应,落到地方就是成千上万亩试验田和车间里的流水线。
紧接着的十月,日本之行为“点火”提供了生动样本。新干线的300公里时速,让随行人员惊叹。他笑称:“就是快,催人跑。”参观日产、松下、新日铁后,他低声嘟囔:“明白现代化是怎么一回事了。”一句话,外人听来简单,实际已定下把国外设备、管理经验请进来的基调。
回国不足两月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会上形成共识:工作重心必须转向现代化建设。这不是凭空落纸,而是南粤、天府、关东多点着火后的水到渠成。多数与会者心里清楚,如果没有那些试验田,没有对“鸭子”“包产”的较真,会议决议会缺少实感。
1979年夏,广东团队提出设立“特殊区域”,利用港澳资本与技术,加快外向型经济。邓小平沉吟半晌,说:“就叫特区,自己去搞,杀出一条血路。”语气平淡,却意味深长——火苗已成燎原之势。
回望1978年的密集行程,会发现一个隐秘逻辑:每到一地,先听抱怨,再给空间,不包办而是催化。政策不再像铁板一块,而像可燃固体,只要一点火星就会释放能量。所谓“我是到处点火的”,说穿了是激活地方主动性的另外一种表达。
这场点火远非拍脑袋。广州试调进口贸易,成都试破农村禁锢,东北试合军民科技;三种路径互为补充,最终融汇进“改革开放”四个字。此后几年,沿海特区、高原承包、内陆联动接连出现,皆源于那年几次看似随意的“吹一吹”。
“火种”仍在传递。如今回到沈阳李德生旧居,桌上的茶渍印已淡,但一句话被很多干部记在笔记本角落:“别怕点火,关键是别让火灭。”
2
鸿岳资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